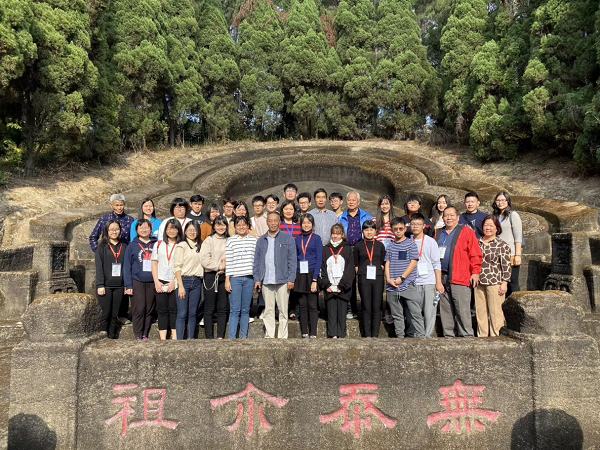|
|
作品名称:《留落在南洋的黄土》 作品类别:征文 作者:陈日弘 年龄:18 所在国/地区:马来西亚 选送单位/社团: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砂拉越总会 留落在南洋的黄土 “来给嬷嬷上柱香吧。” 母亲递来三枝香,我伸手接过,伫立在外婆沉眠了四个年头的坟前。 风,轻轻旋舞而来。烧得正炽的银纸冥钞,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搅动着。烟雾凄迷,火势如蛇信闪缩;翻飞的灰烬,舞上半空,天地一片灰蒙蒙。朦胧间,墓碑上刚髹摹过新漆的字句泛起一抹油亮,而外婆慈祥的脸庞,在脑际蓦地格外明晰起来。那淳朴童年的生活片段依旧历历在目,似一卷经过特别处理的胶卷,影像的纹理分明更胜曩昔。 那是一幅隽永的卷轴,徐徐展开,最初的丹青有着蕉风椰雨当背景。身为典型的旧式妇女,外婆发上梳着圆髻,一身粗布的唐衫陪衬着蝴蝶形的花钮,配上慈祥的微笑,朴实中显得端庄。闲来无事,她就斜躺在藤椅上,而我则坐在矮凳上,听她挥着蒲扇述说那个年代的故事…… “轰隆轰隆的声音,怪怕人的,不是飞机,哪有飞机坐的福气啊! 听见空中航行,不吓得撒尿已好, 炸弹炸下来,你说长眼不长眼? 偷渡的不晓得多少,坐船闷死了、饿死了、病死了,谁可怜?” “那时赤着脚,说什么凉快,还不是图省了个钱。买不起新鞋,破旧的照穿,这里缝缝,那里补补,管这叫穷的象征哪。过年了,什么是新的呢?有,红包呀!裹着几个硬币,高高兴兴地拿到面馆,叫一大碗福建面,可谓人生一大快事啊!” 外婆棒起闻香杯,轻轻呷了一口,茉莉花茶冲出了淡香,她总如此沉淀在自己的记忆里,如茶海里筛不过的渣滓还眷恋紫砂壶怀中的祥柔与暖和。 “南洋这块土地,到底没有黄河奔腾。”这是,沉思中,外婆 的回想。 遥想当年的神州,风起云涌,灾祸频传,稻田欠收,年轻的外婆被迫随着太公登上一艘南下的船,拥抱满怀的黄金梦,带着家人殷殷的叮咛,挥手向亲人道别。她眼中含泪, 遥望着家园无限江山, 对自己说: “我一定会回来的。”哪知世局多变化, 那年一别, 江山从此永诀, 外婆此生注定要在南洋播种殖根, 成家立业, 根移他乡。在外婆眼中,故乡是一团光,光里有山, 山里有水, 水里有声,声里有泪,泪里有叮咛。直至死亡那天, 那光仍亮, 那山仍青, 那水仍清, 那声仍响, 那泪仍热, 叮咛仍在。 怎料当年一船船远赴异乡的炎黄子孙,写下的竟是一首首凄侧悲怆的史诗?满以为从此把枪炮声抛在后头,怎知战火竟烧原而至,席卷了整个婆罗洲,重重的劫难架构成一段梦魇般的岁月。雪上加霜的是,外公的产业遭到友人的觊觎,变卖套现并占为己有。外公经不起半生心血付诸流水的刺激,最终撒手尘寰。外婆悲愤之余,化伤痛为力量,除栽种蔬果,还饲养家禽供售卖以维持生计。为了三个稚子,她挨了一段甜酸苦辣的岁月。 这些历史恰如岳飞的母亲,而外婆则是裸背的岳飞。那段历史就此在她柔韧的皮肉上,刻下了血迹深痕,刻入了痛彻的心肺。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平复了心情,我们驱车前往那让我魂牵梦绕的祖屋。 我忆起外婆陪我翻阅中国杂志的神情。小时候, 无所事事的我总爱跑去祖屋。外婆一见到我,抱起我,说:“乖孙子。”我被她的手弄得痒痒不舒服,鬼叫着要挣脱她的手,她只好顺从的放下我。我瞥见桌上摆放的杂志,就翻开来看,只看里面美丽的图片。外婆看到我翻的图片,就指着那拍得颇有气势的山说: “这是外婆家乡闻名的乌山。风景很美, 里面……”都是一些回忆美化的故事。外婆说完,眼睛盯着那些图片不放,仿佛回到以前故乡秀气的山山水水, 故事正上演。然而,年幼的我听不懂她讲的故事,也无法了解她的心情。我们这些在蕉风椰雨中长大的孩子,又怎能感知大北方那一片浩瀚的山河气概?平日里, 外婆与子孙闲谈,谈着谈着就扯到福州的人和事。外婆拉开嗓子,回味那比酒还醇、比云水还苍茫的陈年旧事,絮絮的话语像一首韵味无穷、久弹不厌的老调。而“福州”这传说中披着神秘外衣的名字, 一早便嵌入了我的心房。如今想起,外婆已去,一切如过眼云烟, 那情那景,我已模糊。 上学了,我记得第一次在地理课本上接触到中国时,有一种无法言喻的亲切和神往,那也许是因为我下意识地将外婆和它联系在一起,间接也把我和它联系起来的缘故吧。后来我在中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一本厚重巨大、色彩绚烂的《锦绣中华》。巍巍娟娟的山川河岳、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龙蟠虎踞的万里长城、花红柳绿的江南胜景,还有那钟灵毓秀的福州三坊七巷,轻易地征服了我的心魂。目醉神驰之际, 我为自己根源自一个地大物博、江山妩媚的文明古国而兴奋自豪。 每年农历九月朔日,镇上欢庆着盛大的九皇爷诞。这期间,居民除了要去上香还愿,还可看闽剧表演。我也凑一份热闹,屁颠屁颠地尾随外婆去目睹这盛况。上香后,便是欣赏闽剧的时刻了。锣鼓声响,戏子一个紧接一个走上戏台,演一出悲欢离合。男人成了旦角,女人摇身变为倜傥小生,舞台上顿时翻起忠奸纠缠的风云变。当时年纪还小,伊伊呀呀的唱腔,我听不明;一板一眼的姿势,我看不懂;让人们沉迷不去的缘故,我亦参不透。可外婆却沉醉于剧情中,神色如同变化莫测的烛火,时喜时忧时怒时困扰时悲痛…… 记得有回戏班演了一出“十年扬州如一梦”,外婆看到伤心处, 黯然泪下。我着实吓了一跳,外婆流泪, 是演员戏好? 还是戏本身惹起外婆藏在内心深处的伤心事? 外婆掏出手帕把眼泪抹了又抹, 泪水最终抹干了。外婆心里的愁, 如果能像泪水, 抹得干干净净, 去得无影无踪,那该多好。但,能吗? 远在互联网尚未发达的年代,一封封印着英女王肖像,越洋而至的浅蓝航空邮筒,驮载了多少外婆在闽的胞姐的孺慕之情? 又密封了多少外婆的幽怨和思念?匆匆数十寒暑, 胞姐已从少女而为人妻、为人母。而两地之间始终横互着千山万水, 彼此唯凭纸笔通消息、报平安。至于胞姐和胞兄的相貌, 则从小就由寄来的照片烙入我心底。 不久,家里安装了电话,我们成功联络到外婆在闽的胞姐。 当听筒传来那陌生又亲切的家乡口音的剎那,也正是外婆一次最直接的心灵交通。外婆紧握着听筒复紧靠着耳朵,口舌因激动而显得笨拙可笑,翻来复去尽寻些不着边际的话来说。可是这有什么关系? 还有什么比两地情牵多年后听见同胞的声音,更令人欣喜若狂? 一切的言外之意,未诉之情,胞姐必然都能一一体会。我在外婆身侧,听着乡亲说着熟悉的福州话,恍惚有种与乡恋共鸣的情感花枝开始疯狂拔节,一股股暖意流入心扉。 “回来吧…….” 从那天起,有种声音一直召唤外婆。她清楚地意识又是那把乡音。回来回来回来……从耳际开始经过耳道,有时幽幽地消失,多数会蹿入脑袋停留一天两天多天,然后爬上头皮,终于驻扎成为神经痛。外婆 “啊!”一声大喊把情绪支离破碎由口腔鼻管统统吐出来,偶尔眼角处迸射出一颗或两颗她却不能确定那到底是剔透的清醒抑或黏糊的梦幻。一天两天, 然后周而复始地又患上思乡症。日子久了,她只愿意称之为思乡情结。迢迢千里, 一别悠悠数十寒暑,壅隔的故乡始终与外婆的梦魂同在,对亲人的悬念未因时空的转移而淡薄,乍断还续的鱼雁往返是一条切不断的脐带,休戚相关, 忧乐与共。唯有归程,那朝夕盼望的归程,却如镜中花、水中月般遥不可及。 车子绕过椰芭、水禾田,越过橡园丘,不一会,就抵达祖屋。 许多景物仍没变,一样的天空,一样的草色。光阴几载,路仍是那黄泥路,可那熟悉的菜圃、鸡寮呢? 怒放的羊齒植物立成剑寒般的阻拦;比人还高的茅草,恣意姿生犹把视线割断。屋顶斜塌了一边,红砖相互推挤着,逼出了几许绿意新芽,在热胀冷缩的光阴中迸裂成皱纹。有蜗牛负着沉重的壳爬上墙垣,却听到一些窃窃私语,如沙漏,更像一声声叹息…… 疮痍的景似利刃,一寸寸地刺戮我己贫血的心房。我到底是莽撞的不速之客呀!思念的泪水,飞不过红砖墙的蕃篱,浇灌不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乡愁在此刻得以偃旗息鼓,像门口那已倒悬的风铃,再不会激起一丝绮念。可外婆呢? 攒了大半辈子,还未及投回神州故土的怀抱,便己顽疾缠身。临终前,她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根,令她遗憾终身的竟是今生无缘重踏故乡的黄土、重踏河山的沧桑。几许栖迟、几许魂牵、几许悲欢、几许遗憾、俱化作了天外云烟。 人的一生,谁不想当个圆月呢?无奈造化弄人,总是缺了个边儿。嬷嬷啊,我知道您终其一生,努力想画个圆,不曾想带恨离去。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嬷嬷啊,我终于明白您这一桩落在红尘里未了的心事。 一朵白色纤柔的蒲公英似有意般飘落在我衣襟,我一手捉起,如抓起一截断梦。若非为势所迫,素来安土重迁的中华儿女,岂想化作一球千羽的蒲公英,展开漫长坎坷的飘泊? 摇呀摇,摇到外婆桥…… 去,去中国闽清,圆梦。
外婆的寿辰
前往外婆家的黄泥路
祖屋后方一角
2019年的冬天,我替外婆踏上归乡的旅途
祭奠先贤黄乃裳
与团队在福州西湖公园合影
福州西湖公园一游
福州金牛山森林步道(福道)风光
游走三坊七巷 |